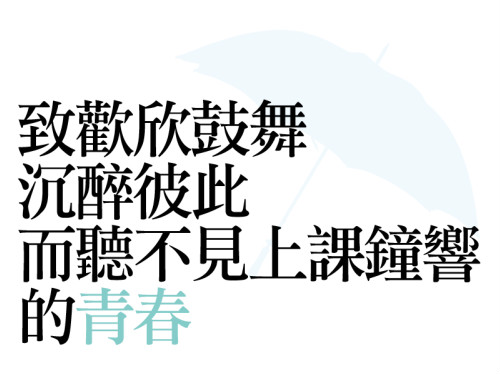
照慣例的行前通知:
*說來就來的致青春番外,有我這麼乖的作者嗎?(求摸摸)(滾吧你)
*番外全是黃瀨的第一人稱,OOC和角色蘇是一定有的,希望各位手下留情。
*本來想寫肉但,肉也放不上LOFTER,所以就拉燈了。這真的不是藉口。(表情誠懇)
*隔了一年重新再寫致青春裡的青黃,覺得很爽快,謝謝各位的閱讀:)
番外一 新井哥
我聽新井哥談過他和一郎的事,是在工作人員慶功宴的二次會上,那時剩下攝影組幾個要好的燈光與場控聚在一塊又喊了瓶日本酒,新井哥幫我推辭幾杯遞過來的燒酒,邊應付著其他人、一面挨著我說:「待會兒我開車送你回去,再等我一下。」
我點點頭,另一邊坐著的是女化妝師正在抱怨前幾天碰見的大牌偶像,仗著事務所名聲響亮對人說話就頤指氣使,我笑著沒回話,這種場合底下說什麼都不對,懂得看人眼色一向是我的強項。她攬著我,從傲慢與偏見談到擇偶條件,從伴侶的必要到應該,從男人三大守則,不菸、不酒、不賭,總結最後,她自暴自棄兩手一攤。
「其實他只要喜歡我就好了,他蠻橫霸道大男人主義都沒關係,如果他能喜歡我,那就好了。」她挨在我肩膀上,腔調帶點哭腔,我趁機問:「小里子談戀愛了嗎?」
她挑眉,「單戀某個人也算戀愛的話?」
「當然算。」我失笑,論單戀這回事我也算是老江湖了,「那我跟小里子就是暗戀陣線聯盟了。」
「你在開玩笑嗎?你用得著暗戀嗎?」她坐直,一臉懷疑又好笑地盯著我,伸手揉開我臉頰的兩團肉,「頂著這張皮的小鬼跟我說他暗戀某個人?我發誓,只要你盯著她,一句話也不用說,把她逼到角落,然後親吻她,她就屬於你了。」說完她作勢欺上來親我的嘴唇,酒氣噴在我臉上,我大笑著躲開,新井哥大手一揮把里子的腦袋拍得遠遠的。
「酒鬼離未成年遠一點!」新井忙著閃避里子張口咬他的攻擊,一群人笑成一團。
新井哥低頭探錶,時針爬到晚間十點零五分,他拉著我的手臂起身,「我還得載小鬼頭回家,你們繼續喝吧,都別太晚回去了。」
大夥嘴裡嚷著新井真不夠意思,卻也沒阻撓或勸酒的意思,我跟在後頭,新井哥走到櫃檯把單買了,面對我疑問的視線只是比了個「安靜」的手勢。上車之後新井哥開了窗,略帶歉意地解釋:「雖然我們沒喝酒,但身上的味道重,開空調可能會比較臭。」
我表示理解地點頭,其實這點事根本無所謂,但新井哥為人稱道的就是細節,他能掌握攝影棚或片場裡最支微末節的小事,舉凡燈架或收音器、工作人員的午餐和新來的2nd AC(*第二攝影助理)寫了幾次場記板,還有我的性向。我至今還是不明白新井哥是怎麼洞悉這些的,單憑我談論青峰大輝的語氣、神態,他只是很小心地輕聲問我:「他和其他人不同,對嗎?」
這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。但我仍然苦笑著答對,青峰大輝和所有人都不同,他特殊得難以定位,有時連我自己都不清楚這真是喜歡嗎?我喜歡他哪裡?新井哥沒有再問下去,他不過是承諾我不會和任何人說出來,因為他也是,我們是一樣的。
新井哥轉著方向盤,駛出銀座的巷弄,「新井哥,我能問件事嗎?」
他沒看向我,但側過臉用鼻音「嗯?」了一聲。
「新井哥是怎麼發現的?」我頓了下,意識到他在等我說完,「呃,就是發現自己是個同性戀……」我才驚覺這話題究竟多不自然,連忙揮手,「不回答也行!就是想問問!」
新井哥笑出聲,「沒事、沒事,你也沒多少人能商量這個,」他沉穩地駕駛,毫不動搖地把問題接下去,「大概是初一吧,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每天我都是第一個進教室的,就是為了從樓上偷看操場田徑社的晨練,盯著那些打赤膊練跑的社員打手槍。」
我發出喉嚨哽住的聲音,新井哥笑得更開了,「聽起來太變態嚇到你了?」
我趕緊搖頭,「我也是一樣的……變態。」承認這很難,新井哥散發的氣質卻讓人能很放鬆地去提它,「我在自慰的時候絕望地發現自己想著他,感覺就像世界末日,為什麼不是別人,偏偏是他啊?那種看起來一輩子對我不會有興趣的人。」
新井哥沉默片刻,我誤認成是否說錯了什麼,正要道歉,新井哥才開口:「你和一郎很像,」他的表情透露出猶豫,卻還是決定把話說完,「不對,你們不同,」他放慢了組織文字的速度,謹慎地處理這個話題,「一郎你見過吧?就是我大學到現在的室友,他知道自己是同性戀的第一個反應是自殺,那才叫真正的世界末日。」
我不自覺屏住呼吸,被新井哥如履薄冰的語氣牽著走。
「一郎自殺過三次,第一次割腕、第二次跳樓,最後一次發生在我眼前,我當時還在片場實習,因為輩份最低,總是要待到最後收拾完才能離開,那天是最晚走的一天,我印象太深了,半夜兩點我回到家,一郎口吐白沫倒在玄關,我以為他死了。」新井哥不曉得注意到沒有,但我看見他捏緊握著方向盤的指節,「我等不及救護車,背著一郎跑過三個街區,送他上急診室手術台之後渾身發抖,醫院診斷他是吞安眠藥自殺,緊急洗胃後躺了兩天加護病房才脫離險狀,這不是最讓我難過的地方,而是一郎住院兩週,沒有一個親屬來看他,起初我以為是一郎不敢通知家裡,我瞞著他打了一通電話,接起來的聲音聽起來像一郎的父親,他誤把我認作一郎的男朋友,咆哮著要我也趕緊去死。」
我說不出話來,新井哥顯然也不認為我能吐出什麼象牙,他講完最後一個字的聲勢咬牙切齒,卻又很快收斂情緒,「所以別說什麼世界末日,黃瀨,你身旁有能理解並支持你的人,這絕不是壞事,我希望你可以因為喜歡上一個人而快樂,無論對方的性別是什麼,你喜歡他,這是最重要的地方。」
我低下頭揉自己的手背,感覺鼻頭有點發酸,我不敢回話,我怕一張口就哭了,新井哥空出打檔的手短暫地摸了幾下我的頭,「有機會的話,真想見見他。」
「見誰?」我抬頭問,新井哥臉上還帶著沒刮乾淨的鬍渣又笑了。
「你喜歡的人。」他說,我鬼叫一聲哀求他別這麼想。事後莫非定律證明了,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,新井哥在GAY BAR和出手救了一郎的青峰大輝終於見上那麼一面。
番外二 青峰大輝
這女兒牆上的磚瓦我都還記得,只是再次造訪的目的與身分和之前迥然不同,我已經來回踱步幾遍,徘徊的次數多到鄰里都準備報警的程度。我抱著胸前的紙袋,腳步茫然地前進、後退,反覆往之,寫著青峰的門牌就在眼前,門鈴離我十公分近。
按吧。
我鼓勵自己,就按下去,沒什麼大不了,應門的不見得是他。也有很大的機率是青峰的母親,這樣我就只要把紙袋裡的衣褲交給她就行,沒錯。就是這樣。我閉上眼按下門鈴,刺耳的鈴聲由屋內響出門外,我別過頭盯著青峰家門前種的一排薑花,正值花期,生長良好的長梗葉同蘆薈般垂青,我聽見腳步聲從走廊傳到玄關。
喀。門打開的聲音異常地響亮。
「進來。」他用命令句,我緩緩扭頭,不敢看他,青峰大輝的臉色比被下牛奶糖禁令的彌子還臭,我戰戰兢兢地送上懷裡的紙袋,「小青峰我今天是來還你衣……」
「進來。」他厲聲重申。
我縮了縮肩膀,「我待會兒還有試鏡,所以……」
「有試鏡的傢伙不會在我家門前站了半小時才按門鈴。」他丟下這句話審判剛才我經歷的一切,下一刻猝不及防地把我往屋內拉,我一個踉蹌險些摔進他懷中,努力保持平衡站定,眼見青峰大輝把門帶上,門閂鎖緊的聲響像把我打入死牢一般令人毛骨悚然。
我試著慢吞吞地脫鞋,客廳傳來青峰母親的聲音:「是誰來了?」
「是黃瀨,之前來家裡住過。」青峰應她,赤裸的視線盯著我從耐吉慢跑鞋離開腳踝、到我脫下後將它們整齊地放在踏墊旁,青峰母親的語氣旋即變得歡快,「好一陣子沒見到了,涼太君!」
她呼喚我的聲調聽起來像聖歌,「伯母我來打擾了!」我溜過青峰身側,小碎步到客廳就看見從沙發站起來的青峰母親,她張開雙臂環抱我,討人歡心彷彿是我與生俱來的才能之一,她貼著我的左臉問:「今天也住下來嗎?」
「不不不!」我驚慌得可疑,希望她沒發覺,「我只是來探望伯母,順便還小青峰衣服,待會兒就離開了。」
青峰母親露出的確能稱之為「可惜」的表情,瞬間湧上來的負罪感令我的頭皮發麻,她放開擁抱我的手,笑著拍了拍我的背,「那我幫你們拿飲料上去吧,涼太君喝麥茶嗎?」
我正要回答她「沒問題」的時刻,青峰大輝當機立斷扔一句:「不用了,我拿就好。」說完他就轉身走向廚房,留下我和伯母面面相覷,她皺著眉,降低了音量說:「大輝這陣子的心情似乎不太好。」
「這樣啊……」我尷尬地彎起嘴角,乾笑幾聲,青峰大輝提著塑料瓶和兩個馬克杯重新出現。他瞪著我,眼神示意上樓,我朝伯母揮揮手,抱著紙袋隨青峰的步伐踏上階梯。每上一格都令我感到胃袋在下沉。
始作俑者是我。青峰大輝壞心情的兇手。我沒忘記口袋裡手機那二十通的未接電話、以及好幾封沒有回信的訊息,而青峰除了殺到我家站崗外能聯繫我的手段都做過,笠松甚至早川學長打來的原因往往令我從震驚到羞愧,他們關心我,以為我和青峰大輝又大吵了一架,笠松學長語重心長地勸,說沒有什麼是籃球解決不了的事,耳殼和話筒間夾雜著學長背後的白噪音,我嚥下口水,回答卡在喉頭。
可是,學長,青峰大輝說他喜歡我,他怎麼能說喜歡我?
學長,我喜歡他,喜歡他的籃球,我曾經就在距離他很近的地方,在他最痛苦的時候,可是我什麼都沒有做,我不知道青峰大輝想要什麼,我給不了他想要的。
笠松學長主動切斷通話之後,我握著手機蹲下來,不明白自己還能怎麼做。青峰大輝轉開房間的門把,我站在廊外,雙腿僵直,踏不出那一步,他注意到我,不耐煩地咋舌,伸手再度將我拉進他的領域裡。青峰關上門,等我反應過來已經被他抵在門板上。
「黃瀨。」他壓低嗓音,猶如某種動物的低吼,「你在躲我?」
他看著我,專注地、一絲不苟地、眼底僅我一人地,我感覺背脊蹭著身後的木板,呼吸宛如被扼住,連吐出一口氣都顯得張狂,我回望他,肯定紅了耳根,「小青峰我……」
青峰大輝沒想要我的答案。他吻我。
「為什麼躲我?」他鬆開我後又問了一次,我挪動雙唇,剛發出一個完整的音節,他又吻上來,順著我張開的嘴連同舌頭一併放進來。
我開始感到惱怒,他在想什麼?我搖晃青峰的臂膀,卻讓他往我的方向迫近,他半摟著我的腰,舔著我的上顎幾乎吻進深處,我們變換著親吻的角度,每一次都吻出水聲,我試著呼吸,青峰大輝的鼻息灼熱地呼在我臉上,掃過因興奮而張開的毛孔。
我們都忘了閉眼,就只是注視著彼此吻開對方的唇。
「小青峰要什麼?」我說,在青峰大輝舔去我嘴角因接吻而溢出口腔的唾液時,走投無路地感受到自己的牙齒在打顫,他尖銳地盯著我,視線像針一般狹長,扎得惱人地疼,「你想要什麼?」
房裡的時間靜止了幾秒鐘,因為青峰大輝似乎動彈不得,我意識到自己紅了眼眶,他很慢、很慢地湊近我,以一種旁人難以察覺到的謹慎縮短彼此的差距,我細算他睫毛的根數與瞳孔的縮放,深色虹膜裡藏的全是我。他頂著我的鼻尖磨蹭兩下,我忍不住闔眼,在感受青峰的唇再次覆上我的之前。
他吻在我唇上,囁嚅著一段話,或是一個詞,在我找到解答時粗魯地擁我入懷,抵著我的肩膀流眼淚。
他抱緊我,彷彿我就是答案。
end
順帶一提青峰出櫃時媽媽的反應是:
「沒有比涼太君漂亮的話就不用帶回家了。」
青峰大輝一時語塞:「他就是黃瀨……」
(長得好看真吃香!←不對吧)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